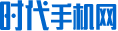藩国身子猛一阵摇晃
身子猛一阵摇晃,脑子里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影像顿时化作一片迷茫。他努力睁睁眼,里面抹了饧,粘稠、浓重,力不从心,只得挣起两只困倦的手去揉,去搓。半天,才给禁锢在漆黑里的两颗瞳仁儿开出一线光明。一个人影儿映入。是谁?混浊的脑水像面久不擦洗的镜子,作不出清晰的判断。
“可醒了!快起吧,高音喇叭吼喊半天了!”
这声音是漂白粉,激浊扬清,顿时化混浊为清澈。原来是她!他倾倾头,耳膜即刻发出如搅和稠粥的震动:
“陆金山!陆金山!赶快回大队来!公社税务所来人了……”
村委会看守蔡三毛患鼻炎,说话瓮声瓮气,扩音器又质劣音噪,声音吻咙咝吻咙咝的,比敲破砂锅还难听。再说,改乡镇村委七八年了,这小子还一口咬住“公社”、“大队”不放,咋检点都改不过口,真使人无法可想……
“我当是甚事哩,哼!来了几要债的!”他翻个身,掖掖被,又合上了眼,身上千虫窜万虫爬,要多难受有多难受。难怪人说“宁惹醉鬼不惹睡鬼”哩,把人从梦中生拉活拽出来,真他妈不是滋味!他怎样努力都回不到梦境,便搜肠刮肚,想一鳞半瓜拾回些残梦碎片。好一阵儿,只想起自打入睡,脑子里就没静过。作过的梦,却如雨落大海,捞不回一星半点。失望之余,他将时间向前推移。现实毕竟不同梦幻,一阵冥索,终于在脑海里捕捉到丝丝涟漪。昨晚是工作队长作的工作报告,题目是:东欧巨变后的形势分析。思绪亦如拆当今流行的编织衣,一旦抓住线头,即可一贯而下。郭队长来下乡快有三个月了。一来就拿出文件要村里派饭,安排住处,像当年社教(四清)工作队一样。咳!也不花钱买上二两棉花纺(访)一纺(访),什么年月了还倒腾那些陈谷子烂芝麻!现如今下乡有几个不是演演样子拉倒,有几个认真到他这地步的?当时秋收太忙,屎紧在 门子上,好说歹说,才讲定交完公粮摊派后再开展他们的工作。昨儿,不能再推了,只得召集下百十来号人让郭队长们过过工作的瘾。平心而论,郭队长真是飞机上的暖壶——高水平(瓶)!讲稿是篇完美的论文!怎奈,里面列举的事件,早在电视、广播里重复过,引不起人们的兴趣。时间一长,人们神疲身乏,拿捏的那点聚精会神便烟消云散,有的哄哄嘈嘈啦家常,有的呼噜呼噜梦周公。他也是硬撑着沉涩的眼皮。左手拇指狠切右手合谷,才没丢盹儿。郭队长沙哑着嗓子宣布报告完毕,他抬头望望墙上黑铜烂铁,比他年龄还大,走时却非常准的飞马牌挂钟:十二点差三分。妈呀!整整用了四个小时。会散后,支村委主要领导又商量了一会儿工作,回家钻进被窝,快凌晨两点了。和被惊醒的妻子没说两句话儿,眼就睁不开了。隐约觉得妻子伸进手来,摸挲那活儿,但蔫不拉几的,立不起茬头。她长叹一声,给自己掖掖被子,转过身去。唉,想不到当了个比芝麻小得多得多的破村长,连夫妻生活都得大打折扣……
“睡不着,就起吧!不是要到心宽家看墙吗?一会儿跟寻到家里来,连饭都吃不好!”妻子进门放下猪食盆,见他两眼花豆豆盯着屋顶,平添了几分怨艾,“罢数椽了,房盖起四年了,连顶篷也顾不上打,还看甚哩!”
昨晚商定,今天早饭后到现场解决李老百姓对此已颇有怨言。所以李显龙总理才会如此高调誓言加大打击贪腐力度。正如新加坡本地媒体在社论中所说心宽和李天亮的界墙纠纷。这一着,他早有所料,前天生产公司预订化肥时就抽空到区土地局和司法局去了一趟。必须立即起身扒两口饭离开,否则,不论什么人来,都会搅得全家不得安生。唉,做饭的热气腾得压栈土发酥,一不留意尘土就掉到锅里。为这妻子没少嘀咕掏挖。顶篷是该尽快打了。他忽地坐起,用迅捷的动作回答了妻子。
三八两口就着老咸菜狼吞虎咽了一个馍,咕噜咕噜蛇吸鲸吞了一碗豆馓馓稀饭,肚子里“咕儿——咕儿——”连打两个饱嗝。他感到无比惬意。少说也有一个月没吃这么熨贴的家常饭了,他多想细细品咂品咂豆馓馓饭的鱼儿香味呀!但时不我待,只得依依不舍溜下炕沿,一步三回头地望着炕上细嚼慢咽的儿子走到屋门前,横横心义无反顾用力一拽。哼隆——门开得异常轻松几乎将他闪倒。原来,等在外面的两口肥猪闻风而动作了配合。两个畜牲齐头并肩奋不顾身往里闯。门框呻吟着发出阵阵颤栗,但还是立场坚定地卡住它们。外面的寒流趁机奔涌而来。“啊——呛!”冷得他连打十六个寒噤外加一个喷嚏。
“贼死下人的挨刀货,出去!出去!”妻子扔下碗筷操起火铲高吆二喝往外轰赶。记吃不记打的畜牲毫不畏惧,嘴里还“吱吱呀呀”哼着进行曲,大有慷慨赴死的气慨。妻子只得改变策略,化干戈为抚慰,端起未晾到适宜温度的猪泔。畜牲们见状奋力拔出身子奔到当院欢呼着胜利。
“记住!碰上买猪的搭照回来。每天光玉米面就得十几斤,迟卖一天赔好几毛哩!”妻子安顿住两个畜牲,进屋叮嘱道。
“唔,唔。”他往身上披着大衣,应道。
“嘿,好大的肥猪!”
闻声,他忙拉门出来。三个税务干部簇拥着蔡三毛已立在当院。
“呵,是荫所长!快屋里坐,屋里坐!”他一眼就认出探出在蔡三毛头上的长马脸,忙迎上去。
“不打扰了。咱来是想核实一下这二年卖的树和交的税是不是相符,请村长给尽快安排安排吧!”
“好说,好说。总得进来喝口水暖和暖和吧?”他心中一悸。
“不了,下午还得跑个村子哩!”荫所长摇摇头,话虽不高,但斩钉截铁。
“那就委屈各位了!三叔,你带伙计们去找富文,让他把卖树的帐取出来让同志们好好查对。顺便告诉来宝,晌午安顿上饭。”
“富文家去过了,不在。”
他搔头想了片刻,把蔡三毛拉到一旁,嗓压低到既能让荫所长们隐约听清,又让蔡三毛相信别人听不见的高度:
“你找个由头到民贵家走走。富文要在,设法儿叫他出来。千万别让人家起疑。”
蔡三毛心领神会点点头,招呼荫所长们往外走。他殷勤送出门,挥手告别:
“中午吃饭时见!”
荫所长回头努力笑笑,没话。另二位头都没回。
荫所长们转个弯不见了。他嘴角忽抽出一丝苦笑,想不到当个村干部,也得有阿庆嫂“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,胆大心细,遇事不慌”的本事才行哩!他蓦然想起有事要办。什幺事,却挖空心思也想不起来,只得转身朝门里喊道:
“翠娥,我今儿有甚事来?”
妻子推开屋门探出梳了一半毛发零乱的头,嗔怪道:
“看你这记性,刚交四十就胡涂成这样了!不是到心宽家看墙去吗?”
“噢——”他恍如梦醒,掉头朝东走去。
到了村尽头,他习惯地向东北大路上望去。远处一个灰色小点拖条硕大无朋的黄尾巴正在移来。显然,那是辆轿车。一冬没下场象样的雪,路上浮土足有寸多厚了,开春后的墒土肯定好不了,现在就该准备春浇了。收眼时,平白如镜的鱼塘冰上十来个奔忙的小黑点儿拖住了他的目光,那是孩子们与客岁同期比拟在玩。“七九河开,八九雁来”,现在已交六九,万一踩塌冰,下面可是丈数深的水啊!他的心不由提了起来。
“金山叔,看甚哩?补才叔让你快去哩!”
“唔,唔”他漫应着,回过身,是团支部书记李栓柱。
“下面那些孩子们干甚哩?”他指指鱼塘。
“啊——”李栓柱手搭凉棚望一眼,“近来每天都有娃子们在那里抽陀螺玩儿。”
“玩什么?”
“陀螺。”
“噢,陀螺,陀螺……”他想起儿子前些天问自己要过这玩艺儿,自己没顾上做,“你下去告诉他们,不要玩了。踩塌冰掉下去出人命哩!”
“唔。你快去吧,补才叔他们急等着你哩!”李栓柱说着踏上下坡的小路。
“哎,你站住!”
“咋?还有事?”李栓柱停步转身。
“中午到来宝家陪陪饭。税务所荫所长他们来了。”
“这……”
村里对陪饭有严格规定:哪方面的客人下来由负责哪方面工作的领导陪。栓柱是团支书,所以感到作难。
“今天特殊,破个例。记住,你提前去把午饭安顿的丰盛点,到时放开海量多灌狗们的几杯。去吧!”
说完,他扭头向北走去。
“我的宅院比他的早圈了十八年!墙是我雇人打的。他李心宽没帮过一锹土,没出过一分钱!再说墙座在批给我的六分大的宅基上。不信,你们可以量!多占出一丝一线,算我输!你们凭什么说墙是伙的呢?”
还没到李心宽新碹的走马青砖大门楼前,李天亮当教师练就的高喉大嗓便敲响了他的耳鼓。
“李老师你别动火嘛!”这是支书刘补才耐着性子的声音,“家有家规,国有国法。各村都有自己的规定。咱村规定合作化以来圈的宅子,占得都是集体的地,不论先后,界墙一律为伙墙,两家都有权在上面盖房。和你说过多少遍了,咋还和人硬僵呢!”
“是家有家规,国有国法。但家规总得服从国法吧?下级总得服从上级吧?我到乡里和区里有关部门查问过了,人家都说像我这情况是禁墙!还说村里的规定是土政策,不作数!”
他心中一凛,暗骂道:他妈的!多少本算不了大问题的事,让这些坐在办公室里信口开河的浑虫们一掺和就复杂了!哼!要不是早有准备,这门一进,就不好出了。
“金山叔,金山叔,等一下!”他正要迈步进门,李栓柱喘吁吁地跑了来。
“啥事?”他抽回脚,愕然问。
“左副区长和农业局张局长下来查看吨粮田来了,让你和补才叔去村委会呢!”
“你到供销社取上包好茶叶和两盒好烟,告诉他们我和补才半小时里准到。”说着,他迈步跨进了李心宽家的大门。
他一露面,在场的人都住了嘴。补才掏出‘迎宾’扔给他一支,没好气地说:
“我还以为你昨晚回家半路上让狼叨走喝了拌汤呢!一大早也不见个鬼影儿。”
他接过烟,笑笑,不置辩。李心宽忙划火柴来点,他掏出气体打火机,啪一声点着。李心宽愣在一旁,火烧到指头肚子了,才疼得裂裂嘴扔掉。李天亮鄙夷地一笑,都哝道:
“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!”
他若无其事地打量一圈院子:山堆的石头和青砖垛把四五分大的院子占了大半。房基上土已垫了二尺多高,南墙上靠立着刮掉皮作椽作檩的新材料,三根一搂粗五六米长的梁材直挺挺顺西墙躺着……难怪李心宽拧住治保会不放呢!原来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了。咳,“鞑子有钱游五台,蛮子有钱胡修盖。”近几年手头稍活泛了点,都你攀我比竟相起房盖屋,改门换庭。由此而产生的纠纷争执不断,令他们村干部头疼心烦,无奈只得定了些简化事态的一刀切的条文。可偏就有不依这条文办事的,李心宽的对手李天亮就是一个。然而,村里想集点资办企业,却没有一个响应的。这种旧观念不改变,要想富起来,还早哪!他胸中顿觉窝了一口气,有点憋闷。
“有屎就屙,有屁就放,你倒是说话呀!”刘补才催促道。
“左区长,张局长来了,要咱俩快去哩!”
“那这里今儿不管了?”
“管,不过要快完,咱就耽搁二十分钟吧。”
二十分钟?治保主任刘黑小摇摇头,心想,吹牛不犯死罪也总该看看牛大小吧!
“好,现在开始。”他把抽了多半截的烟一扔,“黑小哥,看好表,时间一到咱就走。”
在场戴表的都不由抬起手腕看表。
“李老师,我、补才、黑小都是你的学生。记得你一再教导我们学文的要像海瑞,学武的要像岳飞,忠心报国,为民办事。至今,这些教诲我们还时时念叨,勉励自己。”说到这里,他脸一红。当年,他们这几个学生头儿为此写过李老师的大字报,害得李老师在长条凳上没少作柔软体操。他愧疚地看看李天亮,老头儿一脸得色。又回头看看刘黑小、刘补才,二人茫然地点点头。他接着道,“今天,李老师又给我们上了一课,就是‘家规总得服从国法’,‘下级总得服从上级’的道理。弄清这些道理,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李老师,心宽哥,你们说对吧?”
“这还用说吗?”李天亮脸绽成一朵花。
李心宽像霜打的茄子,勉强点了点头。
“李老师说的禁墙的理由我们认为是成立的,根据这些理由判断,没得说,这墙当然是李老师的禁墙!补才哥,烟——”
借伸手要烟,他察看了刘补才刘黑小的表情。尽管他特别强调了“我们”,两人的脸还是沉了下来。他点上刘补才递来的烟,吸了两口,笑问李天亮道:
“李老师,你到乡里和区里反映问题,一准没提村里‘没打墙方应通过协商的办法付给打墙方适当的报酬’这条规定吧?”
“本人争的是这墙的所有权,又不是讨价还价卖墙,提那干甚?”李天亮冷脸道。
“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提了这条规定呢,上级知道村里考虑到了墙的原主,就不会说村里的规定是土政策了。李老师,你说是这个理吧?”稍一顿,他又补充道,“当然,你老不同意村里的规定,咱可另外依国家的法律办。”
“也许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吧!”李天亮答得很勉强。
“既然连李老师也这么说,补才哥,黑小哥,那就证明咱那规定还是对的,你们说呢?”
“那还用说!”
“当然了!”
两人阴沉的脸顿时睛霁。
“对李老师,咱就破个例吧?”
“行!”
“好!”
两人都乐得送顺水人情。
“这……你们……”李心宽抬起垂着的头,急欲争辩,却越急越说不出话来。
共 11942 字 页 转到页 【编者按】通过村里的几件事,可以看出村长的雷厉风行和一贯做法。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村长在一次接待中饮酒过量,而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用陀螺比喻他的人生,死了也要像陀螺那样,不停的旋转。语言富有地方特色,人物的形象较为丰满,整体布局以及人物出场都做了极其细致的安排。【:红荆】
1楼文友: 15:26:56 用陀螺比喻他的人生,再贴切不过了。
宝宝积食腹泻北海治疗白癜风方法醋和大蒜泡脚治灰指甲- 上一篇:藩国这三件古董别人送你再好也不能收很危险
- 下一篇:藩国生命与人生的感悟